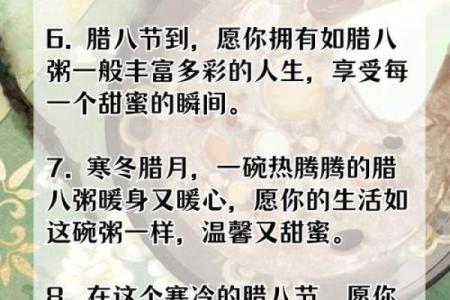讲台上那杯永远冒着热气的茶,大概比任何闹钟都准时。每天清晨七点,走廊还飘着食堂的包子香,办公室的灯已经亮起。我们总说老师像超人,但超人会因为改作业到深夜忘记关台灯吗?会偷偷用红笔在教案本角落画哭脸表情吗?记得她羽绒服袖口总沾着粉笔灰,像落着不会化的雪——那是她蹲在走廊给哭鼻子的学生讲题时蹭到的。
谁没在课间偷瞄过那个神秘抽屉?里面装着褪色的万金油、皱巴巴的糖果,还有比新华字典更厚的家校联系本。有次我发烧趴桌上,她变魔术般掏出退热贴,后来才知道是她常年备着给自家孩子的。午休时总有人溜进去“借”纸巾,却看见压在玻璃板下的照片:二十年前的毕业照里,扎麻花辫的她和现在一样笑出小虎牙。

当多媒体屏幕突然黑屏,她随手抄起半截粉笔的架势,比武侠片里拔剑还帅。板书从三角函数画到清明上河图,粉笔灰簌簌落在她发间,像提前落下的月光。有次课件播到《荷塘月色》突然卡住,她转身写下“田田的叶子”,粉笔与黑板摩擦的声音竟比朗读音频更让人起鸡皮疙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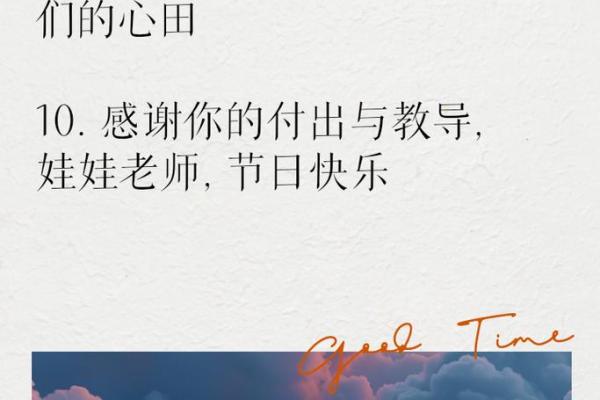
教师节返校时发现,她手机相册存着我们早操时东倒西歪的照片,电脑桌面是去年元旦联欢会被奶油糊脸的截图。当年觉得啰嗦的“注意书写规范”,现在变成甲方夸我合同做得清爽的伏笔;曾经最怕的“课后留下”,如今成了同事羡慕我能快速梳理会议纪要的秘密。教室后墙的光荣榜换了三茬,但窗台上那盆绿萝,依然是她用喝剩的茶水浇出来的倔强。